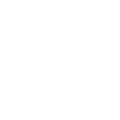我睁开眼睛时,头顶是参天古树交错的枝叶,阳光斑驳地洒在脸上。
海难。我记得巨浪吞噬邮轮的瞬间,冰冷的海水涌入船舱,然后就是无尽的黑暗。
现在,我却躺在松软的沙滩上,身下垫着不知名的阔叶植物。浑身酸疼,但似乎没有重伤。
我挣扎着坐起,环顾四周——典型的荒岛,椰树、沙滩、山峦,望不到边的蔚蓝大洋。
饿了。渴了。
拖着疲惫的身体,我在沙滩边缘的树林里寻找食物。椰子倒是容易找到,但没有工具砸开。就在我用石头费力敲打椰子时,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转身的瞬间,我愣住了。
那是个看起来约莫十四、五岁的少女,蹲在约三米外的树影里。她浑身上下不着寸缕,蜜色的肌肤像抹了层阳光与蜂蜜的混合物。湿漉漉的深褐色长发披散,发梢黏在肩胛和锁骨上。那张脸清秀可爱,五官精致得像是画出来的——杏仁眼、挺翘的小鼻子、饱满的樱唇。只是眼里透出的神情并非人类的警觉或好奇,而是某种……动物般的探究。
她歪着头看我,像一只观察陌生事物的松鼠。
当她缓缓站起身时,我几乎窒息。
少女的胴体发育得极其美好。乳房不大,但形状完美——两座柔嫩的小山丘,顶端是粉嫩得如同花瓣的乳头。腰肢细得仿佛一折就断,小腹平坦,胯部曲线却意外地丰满。双腿修长笔直,像是专门为奔跑跳跃而生的羚羊腿。
最要命的是她双腿之间——那里确实如提示要求,没有任何阴毛,光洁的耻丘下,粉色的肉缝微微闭合着,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。
她四肢着地,像猫一样爬近。鼻尖抽动着在我身边嗅来嗅去,然后发出“呜噜噜”的声音,像是猫科动物满足时的咕哝。
不会说话。她会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——鸟鸣、猴叫、甚至丛林深处传来的野兽低吼。但她对我展示的,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友善。
她拉着我往丛林深处走。动作轻盈如风,赤脚踩在铺满落叶的地面上几乎无声。
她的“家”是个宽敞的岩洞,里头铺满了干草和柔软的植物纤维。她递给我一个剖开的椰子——用手生生撕开的。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,指节纤细但手掌边缘有一层薄薄的茧。
喝水。吃不知名的野果。她坐在我面前,双腿随意张开,完全不在意自己最私密的地方在我眼前暴露无遗。
我硬了。
当然会硬。面前是这样一个赤裸的、美丽的、全无防备的少女,除非我不是男人。
她注意到我胯部的隆起,凑近嗅嗅,然后发出好奇的“唔?”声。她伸手触碰——我抓住她的手。她不解地看着我,眼神纯粹得像一汪清泉。
晚上,她蜷缩在干草堆上睡觉。我躺在不远处,借着洞外月光看她蜷曲的背影。臀部的曲线在月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,两瓣臀肉之间的缝隙隐约可见。
我的手伸向自己裤裆。
第二天,她开始教我在岛上生存。用藤蔓做陷阱捕小动物,爬上树摘野果,在溪边捕鱼——她直接跳进溪水里,像水獭一样灵活地追逐鱼群。
当她从水中站起时,水流顺着她的裸体淌落。阳光透过树冠照在她身上,水珠在皮肤上闪烁。乳头因为水的凉意而挺立,粉色的尖端硬得像两颗小石子。
我把一根手腕粗的树枝掰断,想象那是她的腰。
那天下午,第一次看到了它们。
三只成年大猩猩出现在岩洞附近。我吓得躲到洞内深处,她却欢快地跑出去迎接。为首的雄性大猩猩直立起来至少一米八,浑身黑毛,肌肉遒劲如山。
她抱住那只猩猩粗壮的手臂,蹭着脸颊,像只撒娇的小猫。
然后,那只猩猩的手掌按在她的头顶,向下抚摸,掠过她的背脊,最后停留在她的臀部。巨大的黑掌几乎能盖住她整个臀部。她不但没有反抗,反而发出舒服的“哼哼”声,主动撅起屁股。
我明白了。
所谓“被大猩猩抚养长大”——原来是这样的抚养法。
另外两只猩猩也围上来。一雄一雌。雄性猩猩身高略矮,但同样壮实;雌性猩猩体型稍小,毛色偏棕。
为首的雄猩猩把少女按在岩洞口附近一个光滑的石桌上——那石桌表面磨得光亮,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。少女顺从地趴下,双手撑在石面边缘,双膝分开。
雄猩猩站在她身后,巨大的黑色生殖器从腹下的毛发中探出。
我的脑袋嗡地一下。
那不是人类的尺寸。粗得像我的手腕,长度至少有二十公分以上,暗红色的龟头胀大如拳头。
少女回头看了一眼,眼神里没有恐惧、没有羞耻,只有一种……期待?她甚至主动向后拱起腰,把臀部抬得更高,让那个粉色的肉缝更加突出。
雄猩猩没有立刻插入。它先是用那根东西在少女臀沟里上下摩擦,粗粝的表面刮蹭着她细嫩的臀肉。她发出细碎的呻吟,身体微微颤抖。
然后,它找准位置,龟头顶住了穴口。
少女的喉咙里发出“呜—”的长音,半是痛苦半是愉悦。
雄猩猩缓缓推进。我清楚地看到,少女的肉缝被撑开,粉嫩的穴肉向四周拉扯,努力容纳那根过大的侵入物。她没有流血——显然这不是第一次。
当整根东西插进去大约一半时,少女的呻吟陡然拔高,身体痉挛般抽动。她的腰部凹陷,小腹却微微鼓起——那是猩猩的生殖器在她体内推进造成的轮廓。
雄猩猩开始前后挺动。动作不快,但每一下都深入到底。少女的乳房随着撞击在石桌边缘晃动,乳头硬挺地翘起。
另一只雄性猩猩走到少女面前。它用那双粗糙的手捧起少女的脸,把一根类似香蕉的果实塞进她嘴里。少女含着果实的一端,猩猩则握住另一端,像使用飞机杯一样在她小嘴里抽插。
第三只雌性猩猩也加入进来。它绕到少女身后,伸出细长的手指,探入少女的肛门。
三只野兽同时侵犯她。
少女的身体剧烈地颤抖。她的眼睛翻白,口水顺着嘴角流下,混合着果实的汁液。乳房因为前胸压在石桌上而被挤扁,从侧面溢出柔软的乳肉。双腿之间的蜜穴被雄猩猩的生殖器操干得水声四溅,每一次拔出都带出大量晶莹的黏液,然后再次深深没入。
她的呻吟变成了高亢的尖叫,但又很快被嘴里的果实堵住,变成含混的“呜呜”声。
雌猩猩的手指在她后庭内抠挖,发出噗叽噗叽的声响。
我躲在暗处,裤子已经被自己摸湿了一片。我的手死死抓着岩壁,指甲嵌进泥土。
突然,雌猩猩拔出沾满黏液的手指,从旁边的篮子里抓起一把什么东西——是某种丛林中常见的藤蔓果实,椭圆形的,大小约莫乒乓球。
它把果实塞进少女的肛门。
一颗。两颗。三颗。少女的后庭撑开成一个小圆圈,隐约能看到果实的轮廓。雌猩猩继续往里塞,直到塞进去大概七八颗,少女的后穴明显鼓胀起来。
然后,雄猩猩的抽插速度突然加快。它的低吼声在山洞里回荡。
少女浑身绷紧,蜜穴剧烈收缩,一股清澈的液体从她被操干的小穴里喷溅出来——她高潮了,而且是潮吹。
雄猩猩也在同一时刻射精。它牢牢固定住少女的腰,生殖器在她体内搏动。足足十几秒后,才缓缓拔出。
乳白色的精液混合着少女的爱液,从她被操得红肿的穴口涌出,顺着大腿根部流淌。
雌猩猩把一颗圆润的鹅卵石塞进少女高潮后仍然微微收缩的穴口。然后,它把一根细藤蔓从少女的肛门探入,把那些果实一颗颗往外拉。
“噗、噗、噗——”
果实混着肠液被拉出来,掉在地上。每拉出一颗,少女的后穴就收缩一下,发出羞耻的声音。
她瘫软在石桌上,浑身都是汗水、口水、爱液和精液。乳房在石面挤压下变了形,乳头磨得通红。
三只猩猩离开后,她花了很长时间才缓过劲来。
她从石桌上滑下,双腿发软地走到山洞角落的小水坑边,用手掬水清洗身体。她清洗得很仔细——用手指拨开蜜穴,让水流冲走里面的精液;掰开臀瓣,清洗被塞满果实的后庭。
我看着她清洗自己,看到她蜜穴边缘微微红肿,看到她后穴的小圈一时半会合不拢。
我的手再次伸进裤裆。这次我射了,射在很多,内裤湿透。
从那天起,我成了永久的旁观者。
清晨,天刚蒙蒙亮,雌猩猩会来到山洞。它带着少女到溪边,让她俯趴在溪岸的石头上,双腿分开。
雌猩猩会采集一种阔叶植物的叶子,卷成筒状,塞进少女的蜜穴里。然后含一口溪水,通过叶子往里面灌。
少女的腹部会慢慢鼓起。她咬着嘴唇忍耐,直到灌不下了,雌猩猩才把叶子拔出。然后,它用手指在少女鼓起的小腹上按压、揉捏,让水流在她体内晃动。
最后,少女被允许排泄——大量的水从她穴口喷涌而出,冲走前一天残留的污物。
这是清洁仪式。
上午,少女会去采集食物。但她不只是采集——有时,她会主动找到那只为首的雄猩猩,在它面前跪下,用脸蹭它的生殖器,直到那东西勃起,然后含进嘴里吞吐。
她含得很深,几乎整根没入喉咙。脸颊被撑得鼓起,眼角溢出泪水。雄猩猩会按着她的头,在她嘴里抽插,最后射在她脸上。
她会用舌头舔掉嘴角的精液,发出满足的“嗯嗯”声。
下午是真正的“玩耍”时间。
少女发现了我的一些随身物品:一块从海难中幸存的手表,一个打火机,一把多功能小刀。
她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极大的好奇。
有一天,我看到她把那只手表戴在脚踝上——金属表带恰好勒在她纤细的脚踝上,表盘在阳光下闪烁。她抬起腿,自己欣赏着,然后掰开自己的蜜穴,用表盘光滑的边缘去摩擦阴蒂。
她很快就湿了。透明的爱液顺着大腿流下,滴在草地上。
我递给她一块光滑的鹅卵石。她接过,好奇地看看我,然后似乎明白了什么,把石头抵在阴蒂上画圈。她的呼吸变急促了,另一只手也滑到腿间,两根手指插进蜜穴抠挖。
她跪在地上,屁股高高撅起。手里的石头掉落,她抓起一根手腕粗的树枝,尝试塞进后穴。
塞不进去。太粗。
她发出懊恼的“呜呜”声,转头看我,眼神里竟是求助的意思。
我捡起那根树枝,在她眼前晃了晃,然后指着另一根细些的藤蔓。她眼睛一亮,抓起藤蔓,一头抵住肛门口,缓缓坐下去。
藤蔓顺利滑入。她发出满足的叹息,开始上下移动身体,让藤蔓在肠道里进出。
她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,手指在蜜穴里快速抽插,水声噗嗤噗嗤。
我突然想起背包里还有几个密封袋。我拿出一个,装满溪水,扎紧袋口,做成一个水球。
她看到水球,抢过去,按在自己双乳之间挤压。冰凉的水袋在乳沟里滑动,乳头硬得像两颗小石子。然后,她把水袋抵在蜜穴上,用身体的重量压上去,让水袋变形,凉水刺激着敏感的阴唇。
她高潮了。身体痉挛着倒在地上,水袋破裂,水流淌了一地。
最让我震惊的,是她和猩猩们一起的“游戏”。
那天,我看到她带着两只雄性猩猩和一个……椰子壳。她把椰子壳剖成两半,边缘磨光滑,做成一个简陋的容器。
她让一只猩猩仰躺在地上,然后跨坐到它脸上,蜜穴对准猩猩的嘴坐下去。
猩猩伸出粗糙的舌头,舔舐她的阴部和后庭。她抱着猩猩的头,腰部前后晃动,发出愉悦的呻吟。
另一只猩猩则跪在她身后,巨大的生殖器在她臀沟里摩擦。但没有插入——它在等待什么。
少女突然伸手,把那个椰子壳容器放在自己小腹下方,正好对准蜜穴的位置。
然后,她对身后的猩猩发出某种信号。
猩猩低吼一声,生殖器猛地插入她的肛门——直肠性交。少女发出高声尖叫,但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猩猩的毛发,没有躲开。
身后的猩猩开始在她后庭内抽插。每一下都深入到底,少女的小腹能看到明显的凸起——那是猩猩生殖器在她肠道里的轮廓。
然后,她开始用双手掰开自己的蜜穴,用力挤压小腹。
一股清澈的液体从蜜穴口射出来,正好射进椰子壳里——潮吹,但这次是借助直肠内抽插的刺激造成的。
她连续喷了好几次,直到椰子壳几乎装满。
两只猩猩停下动作。少女摇晃着站起,端起那半椰子壳自己的爱液,走到为首的雄猩猩面前,恭敬地递上。
雄猩猩低头闻了闻,然后伸出舌头舔食。喝完所有液体后,它满意地低吼一声,把少女拉进怀里。
这次的交配格外激烈。
雄猩猩把少女按在一棵斜生的树干上,她从背后插入。巨大的生殖器在她体内横冲直撞,树干都被撞得摇晃。树叶簌簌落下,落在她汗湿的背上。
高潮时,雄猩猩射得太多,精液从她被撑满的穴口溢出,顺着大腿流到脚踝。
那天晚上,我听到她在岩洞里发出压抑的哭声。
我悄悄靠近。月光下,她蜷缩在干草堆上,双手捂着脸。肩膀颤抖着,喉咙里发出小动物受伤般的呜咽。
她其实痛吗?她其实难受吗?只是不会表达?
我伸手想碰她的肩膀。她猛地抬头,泪眼朦胧地看着我。那一刻,我在她眼里看到了某种类似人类的委屈和脆弱。
但她很快又低下头,把脸埋进膝盖间,发出含糊的“呜呜”声,像是在模仿某种悲伤的鸟鸣。
我的手停在半空,最终收回。
从那以后,事情开始变得更……复杂。
雌猩猩开始教她新东西。它带来一根特殊的藤蔓——中空的,有一定硬度,两头开口。
少女很快就明白了用途。
她让一只雄性猩猩躺下,生殖器勃起。然后,她把藤蔓的一端套在那根东西上,另一端放进自己嘴里。
猩猩开始在她嘴里抽插,但通过藤蔓。藤蔓在她口中进出、摩擦喉咙、刮蹭上颚。她能呼吸,但被迫吞咽从藤蔓另一端传来的、猩猩生殖器的气味和预液。
另一个玩法是“套环”。
少女用柔软的藤蔓编成几个大小不同的环。她让我帮忙——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寻求我的帮助。
我们把最大的环套在猩猩的生殖器根部,中等大小的环套在她自己的脖颈上,最小的环则套在她的脚趾上。
然后,当猩猩从背后操她时,她通过拉动套在猩猩生殖器根部的环来控制插入的深度。太深了就拉紧环限制,想要更刺激了就放松。
套在她脖颈上的环则连着一根系在地上的藤蔓。每次猩猩把她往前顶,环就会勒紧她的脖子,造成轻微的窒息感,增强高潮的强度。
最小的脚趾环上挂着几个小贝壳,随着她身体的摇晃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
她玩得很投入。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,嘴角甚至勾起笑容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如此明显的“快乐”表情。
高潮时,她浑身抽搐,脖颈被勒得发红,脚下的贝壳叮当作响。
猩猩射精后,她瘫软在地,急促地喘息着,但脸上是满足的神情。
有时,她会把我当成“道具”的一部分。
让我坐在石头上,双腿张开。然后她背对着我坐下,蜜穴对准我的脸,但保持几公分距离。
猩猩从背后操她时,她被顶得前后晃动,蜜穴在我脸前摇晃,爱液和精液的混合液滴下来,滴在我脸上。
我伸手想碰她,她立刻扭动躲开,发出警惕的“嘶嘶”声。
还有一次,她让我站在溪水里,水没过我的腰部。她则在水面上平躺,双腿分开,让溪水冲刷她红肿的阴部。
我低头就能看到水下,她被操得微微外翻的穴肉在水中轻轻飘荡。
我忍不住伸手想摸。她立刻翻身躲开,溅起一片水花,然后像条鱼一样游远,在不远处露出头,用责备的眼神看我。
我永远碰不到她。
永远。
她属于这个岛,属于这群猩猩。我只是个外来者,一个被好心收留、允许旁观、但永远不能参与的客人。
有一天,我找到了离开的方法。
一场暴风雨后,一艘破损的救生艇被冲上岸。稍微修补,或许能航行到有航线的海域。
我花了三天时间修补小艇,收集食物和淡水。
期间,她一直好奇地在旁边观看。我尝试跟她解释我要走了,指着大海,做出划船的动作。她歪着头,似乎不明白,或者不在乎。
离开前的那个傍晚,我最后一次看她与猩猩们交合。
或许因为是最后一次,这次的情景格外深刻地烙在我脑海里。
她在溪边的空地上,身上涂满红色的泥土——某种仪式。
三只猩猩围着她。她跪在中间,双手被藤蔓缚在身后,眼睛被阔叶蒙住。
雌猩猩先上前,用手指在她蜜穴和肛门里涂抹一种粘稠的树汁。那种树汁带有轻微的刺激性,没多久,少女就扭动着身体,发出难耐的呻吟。
雄猩猩上前,让她张开嘴,往她嘴里塞了一颗奇异的果实。果实散发浓郁的香味,她咀嚼吞咽,很快,身体开始变得异常敏感。
当第一只雄猩猩插入她时,她的尖叫几乎撕裂夜空。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,她经历了也许是有记忆以来最激烈、最漫长、最复杂的一次“使用”。
两只雄性猩猩轮番在她蜜穴和后庭插入。雌猩猩则不停地往她身体里塞各种东西——鹅卵石、小果实、卷起来的树叶。
高潮一次次冲击她。她不断潮吹,地面湿了一大片。尿液也失禁了几次。
最后阶段,雌猩猩用一根中空的竹管,一头插进她的尿道,往她膀胱里灌入掺了刺激性树汁的液体。
灌满后,拔出竹管。少女的膀胱胀得鼓起,小腹圆润如怀孕。
然后,一只雄猩猩从背后插入她的蜜穴,猛烈操干。
每一次深顶,都会挤压到膀胱。尿液不受控制地从尿道口渗出,混合着爱液和精液。
她被操得失禁了,尿液喷溅而出,在空中划出弧线。
她也高潮了,最后一次,最猛烈的一次。身体痉挛得像要散架,翻着白眼,口水流了满胸。
猩猩们完事后离开。她瘫在泥地里,像个被玩坏的人偶。蒙眼的叶子滑落,露出空洞、失焦的眼睛。
过了很久,她才缓缓爬起来,踉跄着走到溪边清洗。
她洗得很慢,很仔细。掰开蜜穴,让水流冲走里面残留的精液和异物;清洗后庭,用手指把残留的树叶渣抠出来;挤压小腹,排空膀胱。
然后她回到岩洞,蜷缩在干草堆上,沉沉睡去。
我坐在洞口,看着月光下她伤痕累累的胴体——乳房上的咬痕、腰侧的淤青、大腿内侧的摩擦伤、微微红肿的阴部。
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。那个在树影下歪着头、眼神清澈如小动物的少女。
我想起了她教我捕鱼、摘果子时天真烂漫的笑容。
我想起了她高潮时混合着痛苦与愉悦的尖叫。
我想起了她哭泣的那个夜晚。
清晨,我拖着修补好的小艇来到海边。
她跟来了。站在沙滩边缘的树林阴影里,赤裸的身体上还残留着昨晚的痕迹。
我向她挥手告别。
她歪着头看我,就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。然后,她缓缓抬起手,模仿我的动作,挥了挥。
喉咙里发出模仿海鸟的“啾啾”声。
我推着小艇入水,翻身上去,开始划桨。
划出几十米后回头看。她还站在那里,深褐色的长发在海风中飘散。
再远些,三只猩猩的身影出现在她身后的树林边缘。为首的雄猩猩伸出手臂,搂住她的肩膀。
她顺从地靠在猩猩毛茸茸的身躯上,眼睛却还望着我离去的方向。
我终于忍不住,对着空旷的大海吼了一声。那声音里有什么,我自己也说不清。
然后我继续划桨,不再回头。
一个月后,我获救,回到文明世界。
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,藏在电脑最深的文件夹里。有时夜里会梦到那片海滩,那个岩洞,那些混杂着淫靡与天真的画面。
我在成人网站上搜索“动物交配”的影片,但没有任何一部能复现那种复杂的感情——那种混合着情欲、嫉妒、怜悯、恶心、以及某种诡异美感的漩涡。
我的硬盘里存了许多“道具”的图片: 藤蔓、卵石、中空的竹管、各种尺寸的环。
我的床头柜里有一根按照记忆中的尺寸定制的硅胶假阳具——模仿那只雄猩猩的生殖器。
有时深夜,我会关上灯,拿出那根假阳具,想象她在岩洞石桌上被操干的样子。
然后我会射精,射在专门准备的小碗里,看着她高潮时被拍下的记忆画面——只存在于我脑海中的画面。
但无论如何,我的手碰不到她温热的身子,听不到她动物般的呻吟,闻不到她混合着汗水、爱液与丛林气息的气味。
我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租了一间公寓,养了一只猫。
猫有时会跳到我腿上,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。我摸着它的背毛,想起她在我身边嗅闻时发出的“呜噜噜”声。
我问自己:如果当时留下呢?
如果我不修那小艇,永远待在岛上呢?
我能改变什么?我能把她从猩猩身边带走?我能教会她人类的语言、人类的羞耻、人类的生活方式?
还是说,最终我也会变成那群猩猩中的一员,用另一种方式使用她?
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,在某个遥远的荒岛上,有一个被猩猩抚养长大的少女,她依然每天赤裸着身子在丛林里奔跑、在溪水中捕鱼、在岩洞里接受野兽的侵入。
她可能还会偶尔想起我——那个奇怪的两足动物,会给她亮晶晶的东西玩,会尝试触摸她但总是失败,然后有一天坐着会浮在水上的东西离开了。
或者,她已经完全忘记。
就像忘记一阵风吹过树叶,忘记一滴雨落入溪水。
就像忘记昨晚被塞进身体的鹅卵石,今早已经排出。
就像忘记高潮时短暂的眩晕,此刻只是平静。
而我,会继续活在文明的世界里,每天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,偶尔在深夜打开那个隐藏的文件夹,想象一片永远回不去的沙滩。
和那个永远碰不到的少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