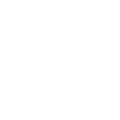接下来的日子变得有些不同寻常。
少女开始主动寻找蚂蚁了。
第一天,是她发现自己在清洗身体时,从沼泽边缘的泥水里捉到的几只红蚁。她原本只是想把它们从腿上拨开,但手指捏住蚂蚁的瞬间,那个想法突然冒出——既然晚上会被蚂蚁刺激得那么舒服,为什么非要等晚上呢?
她坐在沼泽边,看着掌心里的几只小红蚁爬来爬去。细小的脚在皮肤上移动,带来熟悉的酥麻感。她把蚂蚁轻轻放在大腿内侧最敏感的区域。
然后她躺下,等待。
蚂蚁感受到皮肤的温暖,开始爬行。从大腿往上,慢慢接近蜜穴口。那是一种极其缓慢的、若有若无的刺激,比任何手、舌头、甚至蟒蛇的缠绕都要细腻。
她闭上眼睛,感受。
第一只蚂蚁爬到了蜜穴口边缘。第二只爬到了阴蒂附近。第三只还在往上爬,爬向肚脐。
那种感觉太奇特了——不是剧烈的快感,而是无数根最细的针尖同时轻轻地刺、轻轻地刮、轻轻地搔。细微到几乎感觉不到,但加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持续的、难以忍受的搔痒感。
她的呼吸开始急促。
手不自觉地摸向自己的乳房,揉捏,挤压。乳头的硬挺程度让她自己都惊讶——蚂蚁甚至还没爬到那里,但光是想象蚂蚁会爬上去,身体就开始提前反应了。
几分钟后,蜜穴口水开始分泌。起初只是薄薄的一层黏稠透明的爱液,很快变成大量的、涌出的湿润,顺着大腿内侧流下,沾湿了她刚刚放在那里的蚂蚁。
蚂蚁被爱液包裹,挣扎了几下,然后爬得更慢,脚上的黏液让它的移动变成了极缓慢的拖行。
那种拖行的感觉,反而更刺激。
她把腿分得更开,膝盖弯曲,脚底撑着地面,腰部向上顶,让整个阴部区域完全暴露在空气中。然后她用两根手指掰开阴唇,让蜜穴口张开,让更多的空气和光线进入。
她看到蜜穴口的细节:粉红色的黏膜因为兴奋而充血变深红色,一开一合地收缩,像是呼吸。尿道口下方的那颗阴蒂已经完全勃起,红豆大小,深红发亮,表皮光滑紧绷。
还有蚂蚁——一只蚂蚁正好爬到了阴蒂顶端,在那里打转,口器轻碰那颗敏感的小肉豆。
她的身体猛地一颤。
不是剧烈的高潮,而是那种一瞬间的电流通过的感觉,从阴蒂直冲天灵盖,然后迅速扩散到全身,让她整个人抖了一下。
那只蚂蚁似乎也被她身体的震动惊到,停住了,但很快又开始继续爬。
她忍着,让自己完全放松,只感受。
蚂蚁越来越多。不只是她放的那几只,周围的蚂蚁也被她蜜穴口散发的气味吸引过来,开始聚集,开始往上爬。
大腿上、小腹上、耻骨上……密密麻麻的红色小点在移动。
她开始用手辅助——不是驱赶,而是引导。
她用指尖蘸取自己分泌的爱液,轻轻涂在乳头上,然后等待着。很快,蚂蚁爬上去,开始在沾了爱液的乳头上打转,舔食,吮吸。
那种感觉比直接用手揉捏刺激太多了。蚂蚁的吮吸力道很轻,但频率极高,像是无数根最细的针头同时在乳头上高速点刺。
她的腰开始晃动。
不自觉的,无意识的晃动。臀部离开地面,又落下,又离开。膝盖越弯越紧。
喉咙里开始发出细微的声音。
“嗯……”
很轻,像蚊子哼。
然后是第二声:“嗯啊……”
稍微大一点,带着一点颤音。
第三声:“啊……嗯……”
这时候,她控制住了。她知道自己在沼泽边缘,声音会传开,会吸引危险。她咬住下唇,把淫叫声压在喉咙深处,只剩下断断续续的鼻息和压抑的闷哼。
但身体骗不了人。
她的小腹开始痉挛,腹肌收紧,肚脐眼向内收缩。蜜穴口的张合速度加快,爱液的分泌量急剧增加,像泉眼一样涌出,流淌到地面,积成一滩透明的小水洼。
蚂蚁们更兴奋了,像掉进糖罐里,疯狂地舔食那些蜜液。
爬行速度加快,聚集数量激增。
她的阴蒂被至少十几只蚂蚁同时包围、舔舐。那颗小肉豆在密集的刺激下从深红变成紫红,表皮紧绷得像要裂开。
终于,她忍不住了。
腰猛地一挺,臀部高高抬起,整个身体弓成弧形,脖子向后仰,双手抓住身边的草根,手指陷进泥土里。
那高潮来得快、猛、不留余地。
从阴蒂开始,一股强烈的电流爆炸开,瞬间扩散到整个骨盆区域,然后是小腹、胸腔、大脑、四肢末梢。
她的蜜穴剧烈收缩,一股热流从子宫深处喷涌而出——是潮吹,量极大,喷射而出,在空中划出一道透明的弧线,然后洒落在她腿间、腹部,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蚂蚁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液喷射浇了一脸,但很快恢复,继续舔食那些带着蜜糖香味的潮吹液。
高潮的余波持续了很久。
她的身体还在轻微颤抖,蜜穴口一开一合,像濒死的鱼在呼吸。爱液和潮吹液混合在一起,不停地流出,不停地被蚂蚁舔食。
她躺了足足十分钟,才慢慢缓过来。
睁开眼睛,看着灰蒙蒙的天空,眼神迷离。
然后她坐起来,低头看自己的身体。
大腿上、小腹上、乳房上,到处都是红色的蚂蚁,还有它们爬过后留下的细微红痕。蜜穴口湿润红肿,像一朵被揉烂的花。
她又看了看地上的那滩水痕——那是她潮吹的证据。
她伸出手,用手指沾了一点混合液体,送到嘴边,轻轻尝了一口。甜的,腥的,混合起来的味道很奇怪,但她不讨厌。
她笑了。
然后她起身,慢慢走向附近的溪流,清洗身体。洗的时候,她的指尖反复摩擦那些被蚂蚁爬过的区域,像是在回忆刚才的感觉。
那天晚上,我没有去给她滴蜂蜜。
但她自己准备好了。
......
第二天,我早上打开平板,连接手环。
画面显示她在沼泽边缘的树下,正蹲着身子,用一根小树枝小心翼翼地拨弄着什么。
我放大画面。
她在收集蚂蚁。
用一块树皮当容器,用树枝轻轻把泥土里的红蚁扒拉进容器里。动作很轻,很慢,生怕压死它们。
她收集了大概一小撮,几十只的样子,然后站起来,走回她的山洞。
在洞口,她脱下穿着的背心和短裤,叠好放在旁边,然后赤裸着身体坐下。
她先是用手指蘸取了一点昨天剩下的一点蜂蜜残渣——她从什么地方搞到的?我突然想起前天她在榕树林边缘发现的野生蜂蜜,一定是那时候偷偷藏了一点。
她用手指蘸了蜂蜜,开始往自己身上涂。
第一个位置:左边乳头。她用手指仔细涂抹整个乳晕区域,然后乳头尖特别仔细地涂抹了厚厚一层。
第二个位置:右边乳头。
第三个位置:小腹肚脐眼。
第四个位置……她犹豫了一下,然后把腿分开,用手指蘸蜂蜜,开始涂抹自己的整个阴部区域。先是大阴唇外侧,然后是内侧,然后是蜜穴口边缘,然后是阴蒂——她涂得特别仔细,用指尖轻轻地把蜂蜜均匀涂抹在阴蒂的每一个表面凸起。
涂完后,她把那块装蚂蚁的树皮放在身边。
她没有立刻放蚂蚁,而是先躺下,调整姿势,让自己舒服。然后她拿起树皮,开始用嘴唇轻轻吹气,把蚂蚁吹到自己涂了蜂蜜的区域。
蚂蚁们被吹落,掉在皮肤上,先是一阵混乱,然后很快闻到了蜂蜜的味道,开始聚集。
她闭上眼睛,开始等待。
这次没有压抑叫声。
她知道我在看——她知道手环一直在记录。所以她放任自己叫出声。
“嗯……”
从喉咙深处发出的第一声呻吟,很轻,像试探。
蚂蚁开始爬。先是在乳房上,乳头周围的蚂蚁最多,密集得像一团小红云。
“啊……”
声音变大了一点,带着一丝颤抖。
蚂蚁爬到了小腹,钻进了肚脐眼,在里面打转。
“嗯……嗯啊……”
腰部开始晃动,臀部微微抬起。
蚂蚁爬到了大腿内侧,正朝着蜜穴口的方向前进。
“咿……咿……”
声音变尖了,像小女孩撒娇时的呜咽。
第一只蚂蚁爬到了蜜穴口边缘,被蜂蜜黏住,挣扎。
“啊哈……”
喘息声急促起来。
越来越多蚂蚁到达蜜穴区域,开始聚集。
“呜……嗯……啊啊……”
她的声音完全放开了,不再是之前的压抑闷哼,而是完全的、放纵的淫叫。带节奏,带情感,带着对快感的渴求。
她的手开始摸自己——一只手揉捏没涂蜂蜜的左乳房(但上面已经有蚂蚁了),另一只手的手指探进蜜穴口,开始浅浅地进出,配合蚂蚁的爬行刺激。
“嗯……嗯……咿呀……啊哈……”
叫声越来越密集,越来越高亢。
我看到画面里她的身体在颤抖,腿大大地张开,膝盖弯曲到极限,脚趾蜷缩。
蜜穴口已经在不停地流出液体,把蜂蜜稀释,但蚂蚁的数量太多了,舔食的速度超过稀释的速度。
“呜啊啊——!”
终于,第一波高潮来临。
她的身体猛地弓起,脖子向后仰,嘴巴张到最大,发出一声尖锐的、几乎破裂的尖叫。
潮吹喷射而出,量很大,在空中形成细密的水雾,然后落在她腹部、乳房上。
蚂蚁被冲击得四散,但很快又聚集回来。
高潮后,她的身体还在持续颤抖,淫叫声变成断续的呜咽。
但蚂蚁不休息,继续舔食、继续爬行。
她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次高潮,这次比第一次更强烈,身体痉挛到几乎抽筋,手指在自己的蜜穴里快速抽插,发出明显的扑哧水声。
然后是第三次。
每次高潮之间,她甚至连喘息的时间都只有十几秒,就被下一波蚂蚁的刺激推到新的临界点。
第四次高潮时,她的叫声已经变成接近哭泣的哀鸣,眼泪从眼角滑落,混合着脸上的汗水。
第五次最漫长——她的身体像被钉住,一直处于轻微的高潮状态,小腹持续痉挛,蜜穴口持续流出混合液体,呼吸一直停留在最急促的状态。
整个过程持续了至少四十分钟。
她高潮了至少六七次,最后筋疲力尽,彻底瘫软在地上,身体微微抽搐,眼神涣散。
蚂蚁也渐渐散去——蜂蜜被舔完了,它们也吃饱了。
她躺了很久,才慢慢坐起来,眼神放空地看着前方。
过了一会儿,她转过头,看向手腕上的手环镜头。
她的脸上还带着高潮后的潮红,眼睛湿润,嘴唇微肿。汗水把额前的头发都打湿了,一缕缕贴在脸上。
她看着镜头,突然笑了。
不是一个简单的微笑,而是一个……勾引的笑。眼角上挑,嘴唇微张,舌尖轻轻舔过下唇。
她又躺回去,闭上眼睛,继续休息。
我坐在岩石山上的观察点,手里握着的望远镜微微发抖。
屏幕里传来的那些淫叫声,那些高潮的细节画面,还有她最后那个勾引的笑容……
我的裤子又湿了。
但我依然没有下去。
只是继续看,继续录。
......
那天之后,她食髓知味。
每天午饭后,她都会去收集新鲜的红蚁,然后回到山洞,用各种方法给自己涂抹“诱饵”——有时是蜂蜜残渣,有时是她发现的某种甜树汁,有时甚至直接用自己的唾液(但效果不好,蚂蚁不太感兴趣)。
她开始实验不同的涂抹位置。
有时只涂乳头,让几百只蚂蚁同时集中在乳房区域。那种密集的刺激会让她的胸部涨大到极限,乳晕发红,乳头硬到像两颗小石子。
有时只涂蜜穴口和肛门,让蚂蚁集中在最敏感的两个孔周围。最疯狂的一次,她甚至用手指蘸蜂蜜,直接涂抹在蜜穴里面——用手指把蜂蜜抹在阴道壁上。然后她放蚂蚁,那些蚂蚁居然真的钻进去了,在蜜穴深处爬行。
那次的高潮最剧烈,她叫得整个沼泽都能听见,潮吹液喷得最远,量最多,喷射时间最长,持续的高潮让她几乎昏厥。
她也开始尝试不同的蚂蚁种类。
红蚁是她最常用的,但有一天她发现了岛上一种体型更小的黑蚂蚁,移动速度更快,脚更细。她试了一次,那种刺激感完全不同——更密集,更像细微的针扎。
但她觉得太痛,还是更喜欢红蚁。
她还发现蚂蚁的数量有临界点——太少,刺激不够;太多,又太痒太难受,反而会影响快感。她开始学会控制数量,每次用树皮收集大约一百只左右,不多不少,刚好能达到最大刺激但又不至于过度。
她的淫叫声也在这个过程中进化。
现在的叫声已经复杂到我无法用文字完全描述。有长有短,有高有低,有撕裂的尖叫,有呜咽的低吟,有急促的喘息,有悠长的叹息。她会根据蚂蚁爬行的部位调整叫声——乳房高潮时的叫声和蜜穴高潮时的叫声完全不同,肛门高潮时则是一种接近痛苦的、沙哑的嘶吼。
偶尔还会夹杂着我听不懂的词语,从她喉咙里颤抖着飘出来,混合着淫叫声和喘息声,形成一种诡异的、迷人的淫乐。
每天晚上,她也会对着手环表演。
有时是纯粹的自慰,用各种奇怪的道具——树枝、石头、光滑的竹管。有时是和蚂蚁。有时甚至会找一些小动物——比如蜥蜴,她会让蜥蜴在她身上爬行,冰冷的脚爪带来的刺激和蚂蚁完全不同。
她似乎把这当成了日常任务——向镜头后面的我展示她的身体,展示她的快感,展示她如何一步步滑向更深的性欲深渊。
她的眼神也越来越不一样了。
不再是之前那种空洞的、兽性的眼神,而是多了一种……目的性。
她在勾引我,用尽一切方法。
她知道我在看,知道我硬了,知道我想要她。
但她也知道我不会下去——至少现在不会。
所以她继续进化,继续探索,继续用更极端的方式考验我的忍耐力。
......
时间一天天过去。
我的“拍摄”即将结束。
我骗父母说我在“创业公司加班”,其实拿着打工攒的钱来这里。
现在我的存储卡快满了,电池也不多了,而且最关键的是——元旦要来了,那是日本的新年。
父亲前天打电话来,语气很不好:
“你小子要是过年再不回来,以后也别回来了。”
母亲的电话更直接:
“你舅舅介绍了个姑娘,条件挺好的,过年见一面。你要是敢说工作忙,我就跳楼给你看。”
我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。
而且我的存款也快见底了——在岛上生活虽然简单,但设备消耗、日常补给也要花钱。再待下去,我真的会彻底没钱。
我必须回去。
……
我看着平板屏幕里她又一次高潮的画面。
她躺在山洞外的空地上,双腿张开到极限,膝盖弯曲,脚趾蜷缩。腰间系着一条藤蔓,藤蔓上绑着几片卷起来的树叶,树叶里是她提前装好的几百只蚂蚁。绳子的末端在她手里,她可以控制蚂蚁的释放时机。
这次她玩了更复杂的游戏——先把蜂蜜涂满全身,然后控制绳子的拉拽力度,让蚂蚁分批次掉落在不同的位置。
第一批掉在乳房上,她高潮一次。
第二批掉在小腹上,她又高潮一次。
第三批直接掉在蜜穴口上,她高潮得最剧烈,手指在自己的蜜穴里快速进出配合,潮吹液喷射得整个肚皮都湿透了。
高潮后,她对着镜头,做了个邀请的动作。
我知道她是认真的。
她知道我硬了,知道我快要忍不住了。
但我也知道,我不能碰她。
太脏了。被那么多野兽用过,被蚂蚁爬过,被蟒蛇缠绕过,被关在岩洞里当性奴过。
哪怕她再美——蜜色的光滑皮肤,修长的腿,饱满挺翘的乳房,那张即使在荒岛生活这么久依然保留着少女柔美特征的脸。
我还是觉得……脏。
这个字在我脑子里扎根太深,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。
但我必须回去过年。必须面对父母的催婚。必须假装自己在城市里有正经工作,有正当收入,有光明的未来。
然后一个想法突然冒出来。
如果……我带她回去呢?
让她扮演我的女朋友,帮我对付父母的催婚。
她很漂亮,这一点绝对够格。而且她不会说话。我可以编一套故事:说她是从东南亚来的,我们通过网络认识,她来日本找我。
听起来很扯,但我父母估计也不会深究——只要我带回来一个活生生的、漂亮的女孩,他们就满足了。
但这个想法下一秒就被我自己否决了。
她肯定会坏事。
说不定第一天就在我家客厅脱光衣服,用厨房的糖浆涂在身上招蚂蚁。
说不定对我父亲勾引。
说不定对着邻居学猴子叫。
光是想想就觉得头皮发麻。
还是算了。
......
但我没想到,意外比计划来得快。
在我要离开的前三天,她感冒了。
岛上连日降雨,沼泽地区气温骤降,又是冬季,哪怕热带地区的岛屿,也会又湿又冷。她那个浅山洞根本挡不住寒气。加上她常年赤裸身体,抵抗力本来就差。
第一天她只是咳嗽。
第二天开始发烧。
第三天,她躺在山洞里,几乎起不来了。
我通过手环的体温监控看到,她的核心体温已经升到三十九度五,还在继续升。嘴唇发白,皮肤发烫,呼吸急促,整个人处于半昏迷状态。
她需要退烧药,需要抗生素,需要治疗。
而我没有。
我的医疗包里只有创可贴和酒精棉片,最多还有几片止痛药,而且过期了。
怎么办?
看着她一个人躺在那里,烧得迷迷糊糊,有时还会在昏迷中抽搐,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呜咽声……
我做不到放下她不管。
第四天凌晨,我做了决定。
我带她走。
偷渡的方式。
......
那晚下着大雨,沼泽地区气温更低。我等到深夜,穿上所有能穿的防水衣物,带上背包,悄悄潜到她山洞。
她状态很糟。
躺在地上,身体蜷缩成一团,浑身发抖。嘴唇干裂,脸颊通红,额头上都是汗。手环显示体温四十度一。
她睁开眼睛看到我,已经烧到神志不清了。
“呜……”她发出细微的呜咽声,手伸向我,不是求欢,是求救。
我蹲下身,检查她的状况。
呼吸很浅,脉搏快而弱。她的身体滚烫得像火炉。
我快速给她套上我的备用衣物:一件T恤,一条长裤,一件厚外套。她完全不配合,身体软得像滩泥,我只能费力地给她穿上。
然后我把她背起来。
她很轻——在岛上生活太久,营养不良,加上发烧脱水,体重可能只有八十斤出头。
我背着她,走出山洞,朝着岛上另一侧的“秘密码头”走去。
那是我当初登岛的地方,藏着一艘小型充气皮划艇,还有一小桶汽油。那是我的逃生设备,我一直藏着,连岛上其他人都不知道。
雨很大,路很滑。丛林里的植物在黑暗中像无数只手在拉扯我,试图让我放弃。
但我咬着牙继续走。
她在我背上,头靠在我肩膀,呼吸灼热地喷在我脖子上。有时她会发出微弱的呻吟,声音很小,但我能听出来是痛苦的呻吟,不是性快感的呻吟。
“坚持住。”我用极低的声音说,“快到了。”
我知道她听不懂,但她似乎感受到了,手臂用力地搂紧我的脖子。
三个小时后,我们到达海岸边的秘密码头。
我把她小心地放在皮划艇里,用防水布盖住她大部分身体,只露出口鼻呼吸。然后我启动引擎,那艘小小的充气艇在暴雨和黑夜中,朝着最近的陆地驶去。
一路上,她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。
有时会浑身抽搐,我会停下来检查,摸摸她的额头,喂她一点水。
有时她会突然睁开眼睛,眼神涣散地看着我,然后莫名其妙地开始淫叫——发烧让她的脑子混乱了,她把我的触摸当成性刺激。
“嗯……嗯啊……”她发出细微的声音,手伸向我裤子。
我轻轻按住她的手,摇头。
她会困惑地看着我,然后眼睛又慢慢闭上,继续昏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