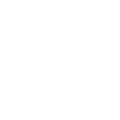六个小时后,天快亮时,我们到达最近的一个小渔村。
我把船藏在隐蔽的礁石后面,背着她,像背着生病的妻子或情人,走向村子唯一的小诊所。
那个诊所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乡村医生,姓后藤。我听说过他的名声,据说他年轻时在东京的大医院工作过,后来因为什么“医疗事故”被开除,回到老家开这个小诊所。
敲开门时,后藤医生刚起床,穿着睡衣。
看到我背着一个昏迷的女孩,他愣了一下,然后赶紧让我们进去。
诊所很小,典型的日本乡村诊所,只有一间诊断室,旁边是药房,最里面有一张简易病床。
我把她放在病床上,喘着气说:“她发烧,很严重。在野外淋雨了好几天。”
后藤医生戴上老花镜,开始检查。听心跳,量体温,看瞳孔,检查喉咙。
“四十度三。”他的表情严肃,“肺炎前兆,可能已经感染了。需要抗生素和退烧药,还要打点滴。”
我点头:“钱我有,您尽管用。”
后藤医生让我去外面等着,他要给她打针。
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,后藤医生才叫我进去。
她已经打了退烧针和抗生素,手上挂着点滴,睡着了。脸上的潮红退了一些,呼吸也平稳了很多。
“要住院吗?”我问。
“最好是住一两天。”后藤医生说,“但我这里没有住院条件。不过……”他想了想,“如果你信得过我,可以让她在这里躺两天。我家就在隔壁,有什么事随时过来。”
我犹豫了。
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?
但我也没别的选择。我先要回父母家应付父亲母亲,而且还要想办法给她弄个假身份,总不能直接带她去我家。
“好,拜托了。”我说,“谢谢后藤医生。我去镇上办点事,傍晚回来。”
我留下一些钱,又留下我的手机号码,然后走出诊所。
但走到门口时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后藤医生正站在病床前,低头看着床上熟睡的她。
他的眼神让我心里一凉。
那不是医生看病人的眼神。
那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。而且是很久没有碰过女人的、饥渴的老男人的眼神。
他六十多岁,瘦高,皮肤蜡黄,脸上布满皱纹和老年斑。手指因为常年吸烟而发黄,微微颤抖。
他盯着她裸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臂,盯着她的颈项曲线,盯着她因为呼吸而微微起伏的胸部。
他在吞咽口水。
我看到了。
但我什么都没说,还是走出了诊所。
我必须先回父母家。必须去见父亲母亲。必须编一套谎言解释我为什么消失这么久。
而且……我内心深处,有个黑暗的想法在冒头。
让她留在这里,被那个老变态医生看,甚至可能被他摸……
那种感觉很复杂。不是嫉妒,不是愤怒,而是一种……扭曲的好奇心。
我想知道,如果他真的对她做了什么,会怎么样?
她会反抗吗?会因为生病而无力反抗吗?还是会像对所有雄性那样,张开腿欢迎?
我想知道。
这想法让我自己都恶心,但我还是开车离开了。
朝着父母家的方向。
......
傍晚,我回到父母家。
两层独栋木造住宅,典型的日本郊区一户建。周围都是类似的房子,社区关系紧密,邻里闲话传播极快。
我一进门,就被母亲抱住,眼泪流了我一脸。
“臭小子!这么久不回家!你知道妈妈多想你吗!”
父亲站在后面,板着脸,但眼神里的关心藏不住。
“工作有这么忙吗?电话也不接。”
我编了一套说辞:公司新项目紧,我负责核心模块,天天加班通宵,手机常驻公司充电。
“钱呢?”父亲问。
“有的,这个月刚发奖金。”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厚厚一叠现金,“给妈的,买点好吃的。”
母亲的眼泪更多了:“就知道你孝顺。”
晚饭时,催婚话题如期而至。
“铃木阿姨家那个姑娘真的不错,大学老师,长相也秀气,家庭条件也好……”母亲开始列举那一百零八条优点。
“我有女朋友了。”我打断她。
两双眼睛同时瞪大。
“什么?”
“什么时候?”
“谁家的闺女?”
“怎么不带回来看看?”
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打过来。
我慢慢说:“是外国人,东南亚那边的。我们在网上认识的,她最近刚来日本找我。本来应该带她回来,但她生病了,在医院。”
母亲立刻紧张:“生病?什么病?严不严重?在哪家医院?我去看她!”
“不用不用。”我赶紧说,“小感冒,在镇上诊所挂水。明天就好。明天我带她回来。”
父母对视一眼,眼神里有怀疑,有期待,有担心。
但终究是欢喜的——儿子带女朋友回来了,管她是哪国人,带回来就行。
那天晚上,我睡在新装修的卧室里,辗转反侧。
脑子里全是她躺在诊所病床上的样子。
她的烧退了吗?
那个后藤医生对她做了什么吗?
他现在在做什么?
凌晨两点,我终于忍不住了。
悄悄起床,穿上外套,蹑手蹑脚走出家门。
开车前往镇上的诊所。
......
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。
我悄悄把车停在诊所后面的小巷,然后绕到诊所侧面。诊所有两个门,前门对着大街,后门对着一个小庭院。
后门锁着,但窗户没关严。
我推了推,窗户开了够一个人钻进去的缝隙。
我钻进去。
诊所里很黑,只有诊断室里亮着一盏昏暗的小台灯。
我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往里走。
走到诊断室门口时,我停下,躲在门框后面,往里面看。
她还在病床上,睡着了。
点滴已经拔了,呼吸平稳很多,应该退烧了。
但她没有盖好被子——被子只盖到腰部,上半身赤裸着,乳房完全暴露在空气中。乳头因为夜晚的凉意而微微硬挺。
她的手被绑住了。
用的是白色的医用绷带,缠绕在手腕上,然后固定在床栏杆上。绑得不紧,但足够让她无法挣脱。
后藤医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
他脱了白大褂,穿着背心和短裤,赤裸着两条干瘦的老腿。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,正对着她的身体照。
手电筒的光束很细,很亮,在她肌肤上缓慢移动。
先照在她脸上,让她在睡梦中皱眉,转过头躲避光线。
然后往下,照在脖子上,锁骨上。
再到乳房。
光束在乳晕上停留了很久,然后聚焦在乳头。乳头在强光刺激下微微收缩,变得更硬。
后藤医生伸出那只颤抖的、布满老年斑的手。
他很轻地、很慢地摸过去。
指尖先碰到乳晕的边缘,然后慢慢向乳头中心移动。
她的身体在睡梦中微微颤抖了一下,但没有醒。
后藤医生的手指按住了乳头。
先是轻轻的按压,然后开始旋转、揉捏。
他的呼吸开始急促,另一只手摸向自己的裤裆,那里已经鼓起一个小包。
他在自慰。
一边摸她的乳头,一边自慰。
我躲在门外,看着这一幕。
身体里有两种情绪在打架:一种是想冲进去打断他,救她;另一种是……想看。
想看这个老变态会做到什么程度。
想看她的身体在睡梦中如何反应。
那种扭曲的好奇心压过了道德感。
我继续看着。
后藤医生的手从她的乳头往下移,滑过她的小腹。小腹平坦,有微微的腹肌轮廓。
他的手在肚脐眼停了一会儿,然后继续往下,来到她裸露的下体。
她没穿内裤——应该是后藤医生在给她检查时就脱掉了。
她的手环还戴在手腕上,银色的金属在灯光下反射着微弱的光。
后藤医生的手指轻轻分开她的阴唇。
她蜜穴口的画面在我的方向看得很清楚:粉红色的黏膜,微微张开,因为发烧和之前的性兴奋,依然保持湿润。
后藤医生舔了舔嘴唇。
他蹲下身,脸凑到她的双腿之间。
他闻了闻。
很轻的,像狗一样嗅气味。
然后他用手指轻轻拨开阴唇,让蜜穴口张得更开,然后他伸出舌头。
舌尖很轻地碰了碰蜜穴口的边缘。
她的身体猛地一颤,在睡梦中发出一声细微的呻吟。
后藤医生吓了一跳,立刻抽出舌头,直起身,观察她的反应。
但她没有醒,只是眉头皱得更紧,身体扭动了一下,然后又沉沉睡去。
后藤医生等了一分钟,确定她没醒,又蹲回去。
这次他更大胆了。
双手抓住她的大腿,分开到极限,然后他的脸完全埋进她的双腿之间。
我听到了舔舐的声音。
很轻,但很清晰。
她的身体开始有反应。
即使在熟睡中,即使在生病中,她的身体记住了被舔舐的感觉。
她的腰开始轻微地晃动,大腿肌肉紧绷,脚趾蜷缩。
喉咙里发出细微的、压抑的呻吟。
“嗯……”
很像她平时高潮时的声音,但更轻,更无力。
后藤医生更兴奋了。
他舔得更用力,舌头更深入,甚至用手指辅助——两根手指探进她的蜜穴,浅浅地抽插,同时舌头继续舔舐阴蒂。
他显然经验丰富,虽然不是年轻时的水平,但知道该舔哪里,该用什么节奏。
她的反应越来越强烈。
呼吸变急促,腰晃动的幅度变大,呻吟声也从低吟变成明显的高潮前兆。
“呜……嗯啊……”
终于,她的高潮来了。
睡梦中的高潮,来得突然又猛烈。
身体猛地弓起,但被手腕的绑缚限制,只能弓到一定程度。脖子向后仰,嘴巴张开,发出一连串短促的、压抑不住的呻吟。
蜜穴剧烈收缩,爱液大量涌出,喷在后藤医生脸上。
老医生抬起头,脸上湿漉漉的,表情既满足又贪婪。
他用手抹了一把脸,把那液体送到嘴边尝了尝。
然后他直起身,解开自己的裤腰。
他老了,生殖器瘦小,软塌塌的。但他开始手淫,想让自己硬起来。
眼睛一直盯着她高潮后的身体——还在微微痉挛,蜜穴口一开一合,爱液缓缓流出。
他一边自慰,一边又蹲下去,继续舔。
她很快又迎来了第二次高潮,这次比第一次更剧烈,叫声更大,身体痉挛的程度更夸张。
后藤医生在她第二次高潮后,终于硬了——但硬度远不如年轻人,只是勉强能插入的程度。
他爬上病床,抓住她的大腿,对准她还在溢出爱液的蜜穴口,准备插入。
我看着他,看着他那个衰老的身体准备强奸一个昏迷的女孩。
但我依然没有动。
因为就在他准备插入的那一刻,她的手——虽然被绑着,但手指能动——突然主动抬起,抓住了他的手。
不是推开。
是拉近。
她睁开眼睛,虽然眼神还迷离,但明显是醒了。
她看着他准备进入她的身体,突然笑了。
然后她张了张嘴,用口型说了几个字。
我看不懂,但后藤医生显然看懂了,愣在那里。
她又说了一遍,同时抓着他的手,引导他往她的蜜穴口按。
后藤医生试探着把龟头抵在蜜穴口。
她点点头,腰向上顶,主动把蜜穴口迎向他。
她想要。
哪怕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变态,哪怕是在病床上,哪怕还在发烧。
她想要性。
后藤医生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,开始慢慢地插入。
很慢,因为他的硬度不够。
她微微皱眉,似乎对这种缓慢的、软绵绵的进入不满意。
她的手虽然被绑着,但可以移动。她抓住他的臀部,用力往下按,想让他进入得更深更快。
后藤医生吃力地进入,终于整根没入——他的长度也有限,进入得不深。
然后他开始缓慢地抽插。
频率很慢,力度很轻。
她躺在床上,眼神迷离地看着天花板,身体跟着他缓慢的节奏晃动。
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呻吟,不是高潮时的激烈,而是那种淡淡的、无力的哼鸣。
她似乎在等,等高潮的来临。
但后藤医生的速度太慢了,力度太轻了,她一直无法到达临界点。
她开始不耐烦。
腰部开始大幅度地主动扭动,试图自己加快频率。
她的淫叫声也开始变大,从细微的呻吟变成明显的、连续的“嗯……啊……嗯……啊……”
但后藤医生已经到极限了,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。
他坚持了大概五分钟,终于忍不住,在她体内射精了。
量很少,射完后立刻软掉,抽了出来。
他瘫在她身上,大口喘气。
她看着他,眼神里有明显的失望。
然后她抬起那只被绑的手,指了指后藤医生已经软掉的生殖器,又指了指自己的蜜穴,然后做出一个“不要”的手势。
像是在说:你不行。
后藤医生看懂了这个手势,脸色变得难看。
但他太累了,只能从她身上下来,坐在床边继续喘气。
她扭动身体,想自己解决——但手被绑着,无法直接摸到。
她看向自己的蜜穴口,那里还缓缓流出混合液体。
她想了想,突然把双腿高高抬起,架在床尾的栏杆上,然后腰部用力,开始前后摆动。
她用腰臀的力量,让蜜穴口在空气中摩擦——虽然没有实质性插入,但光是肌肉的收缩挤压,也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。
我看着她自己在病床上用腰臀动作自慰。
淫叫声越来越大,越来越急促。
后藤医生在旁边看着,想帮忙但已经没力气了。
终于,在她持续了三分钟的剧烈扭动后,她达到了高潮。
这次高潮比之前两次都强烈——也许是因为她一直在边缘徘徊,积累的快感更多。
身体剧烈痉挛,双腿在空中乱蹬,脖子向后仰到极限,嘴巴张开,发出一长串尖利的、几乎破音的尖叫:
“咿呀——!啊啊啊——!呜哇——!”
大量潮吹液喷射而出,在空中形成一道明亮的弧线,然后洒在她自己的腿上、腹部、乳房上。
她高潮了很久,身体持续颤抖,最后才慢慢平复。
躺回床上,大口喘气,眼神涣散地看着天花板。
后藤医生在旁边,看着她的身体,又看看自己软掉的生殖器,表情极其复杂。
然后她转过头,看向后藤医生,突然又笑了。
她伸出那只被绑着的手,对着他,勾了勾手指。
像是在说:再来一次。
后藤医生吞了口口水,看看她,又看看自己的下半身,犹豫了一下,然后开始再次尝试自慰。
但这次,她不等他了。
她继续自己扭动腰臀,开始第二轮高潮前的积累。
淫叫声又一次响起,在深夜的诊所里回荡,混着后藤医生急促的喘息声。
我站在门外,看着这一幕,裤子已经完全湿透。
我想进去,想推开那个老变态,想自己上她。
但那个“脏”字,还是像绳子一样捆住我的脚。
我看着,继续看着。
看着她她在病床上一次一次高潮,看着那个老变态医生一次一次失败,看着她越来越不满足的眼神。
直到天亮。